在北京幾個小區(qū)走訪調(diào)研時,北規(guī)院弘都規(guī)劃建筑設(shè)計研究院的趙琳發(fā)覺,像氣候變化這樣的宏大概念,到居民生活中其實是非常具體甚至瑣碎的“小事”。
“夏天熱得不能出門”“樹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車”“冬天出小區(qū)門會被冰滑倒”“暴雨后滲水漏水”……她發(fā)現(xiàn),正是這些細節(jié)構(gòu)建起了社區(qū)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的最小顆粒,同時也切身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方式。
但當(dāng)災(zāi)害真正來臨時,日常的小事又可能演變?yōu)橐粋€個風(fēng)險點——高溫天、樹木倒伏、暴雨后內(nèi)澇的小區(qū)、被水淹沒的車庫和滲水的室內(nèi),以及平時不起眼的電線桿和充電插頭,此時也可能變得致命。
視角轉(zhuǎn)到更大尺度,面臨風(fēng)險的社區(qū)在國內(nèi)是普遍存在的,基礎(chǔ)條件也千差萬別。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無論身在何處,社區(qū)和社區(qū)中的居民都已無可避免被卷入這一場氣候變局中了。
近日,澎湃新聞采訪多名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?qū)<覍W(xué)者,共同探討面對極端天氣時,個體觀念該如何轉(zhuǎn)變,與之緊密相聯(lián)的社區(qū)可以做些什么,以及城市中的不同角色如何實現(xiàn)協(xié)同溝通、精細化地治理城市。
一、當(dāng)城市面臨挑戰(zhàn) 我們的城市正面臨新的挑戰(zhàn)。
繼2023年成為有記錄以來的最熱年份后,世界氣象組織6月發(fā)布報告稱,未來5年,至少有一年超過2023年熱度的可能性高達86%。據(jù)IPCC報告預(yù)測,全球平均氣溫將持續(xù)上升,熱浪和強降水等極端天氣的發(fā)生頻率也將持續(xù)上升——湖南洞庭湖干旱與洪澇的兩極境遇、廣東梅州高速深夜塌方、四川雅安泥石流、陜西省商洛突發(fā)暴雨山洪致橋梁垮塌、湖南資興暴雨泥石流......
“以前五十年一遇、二十年一遇的災(zāi)害,現(xiàn)在可能提高到十年一遇、五年一遇,發(fā)生的頻率更加頻繁,這種增加的趨勢還是加速的。”“卓明信援”創(chuàng)始人郝南盤點今年同類型的災(zāi)害說,盡管暫時沒有2021、2023年那種特大災(zāi)害,但今年氣象災(zāi)害的密度和強度還是很不同尋常,從今年4月起,廣東等地就已經(jīng)開始受到洪澇災(zāi)害的影響,從6月起,全國范圍內(nèi)幾乎每天有兩個以上的地區(qū)正在經(jīng)歷災(zāi)情。
在越來越難以預(yù)料的天氣面前,擁有龐大存量住房和人口基數(shù)的城市顯得有些“笨拙”,其脆弱性日益引發(fā)關(guān)注。
中國城市規(guī)劃學(xué)會城市安全與防災(zāi)規(guī)劃專業(yè)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、南京大學(xué)建筑與城市規(guī)劃學(xué)院教授翟國方在“2024中國城市規(guī)劃年會之專題會議”上,提到了國內(nèi)城市應(yīng)對災(zāi)害的嚴峻形勢。
“中國有75%的超大城市、80%的特大城市位于7度以上地震高風(fēng)險區(qū);有很高的洪澇危險性,我國現(xiàn)有城市657座,均不同程度受到過江河洪水、臺風(fēng)暴雨、山洪泥石流以及局地暴雨等洪澇災(zāi)害的威脅等。”
翟國方提到,此外,城市還存在災(zāi)害暴露度大,人口、經(jīng)濟暴露度大的特征。
據(jù)國家統(tǒng)計局發(fā)布《2021年國民經(jīng)濟和社會發(fā)展統(tǒng)計公報》顯示,2021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(zhèn)化率為64.72%,同時城市也是區(qū)域政治中心、教育科技中心,一旦發(fā)生災(zāi)害其影響非常巨大。另一方面,當(dāng)前城市防災(zāi)減災(zāi)救災(zāi)能力較低,包括城市防災(zāi)能力比較低、應(yīng)急疏散救援空間比較少、城市韌性區(qū)域差異比較大、城市災(zāi)害應(yīng)對橫向聯(lián)動機制比較弱和居民風(fēng)險意識比較弱。
翟國方從事韌性城市相關(guān)研究已有二十余年,見證了國內(nèi)政策的變更。不過,在政策往下落時,效果不一定理想。
在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領(lǐng)域,2013年,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會同相關(guān)部門發(fā)布《國家適應(yīng)氣候變化戰(zhàn)略》;2014年,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會同相關(guān)部門發(fā)布了《國家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規(guī)劃(2014-2020年)》;2020年,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部、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等17部門聯(lián)合印發(fā)《國家適應(yīng)氣候變化戰(zhàn)略2035》。
在城市層面,德陽、北京等城市先后編制韌性城市專項規(guī)劃。但在社區(qū)層面,目前國內(nèi)缺乏以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為導(dǎo)向的能力建設(shè)行動指引。
翟國方注意到,2019年后,相關(guān)政策中有關(guān)防災(zāi)減災(zāi)、安全韌性等方面的內(nèi)容明顯增多,關(guān)注點也不再單一強調(diào)房屋建筑安全,而是轉(zhuǎn)變?yōu)閷Πㄖ踩⒒A(chǔ)設(shè)施建設(shè)、防災(zāi)應(yīng)急管理在內(nèi)多領(lǐng)域、多層面的關(guān)注。然而,在城市體檢相關(guān)的制度策略、應(yīng)急預(yù)案制定等方面的關(guān)注略顯不足。
“更新過程中存在的很多問題盡管已有應(yīng)對措施或標(biāo)準(zhǔn),但未實施到位,或者有了措施和標(biāo)準(zhǔn),但這些已落后于新形勢的要求。”翟國方說,比如超高層火災(zāi)和電瓶車引發(fā)的火災(zāi)便是技術(shù)發(fā)展帶來的新災(zāi)害形式;在工程建設(shè)上,類似情形有城市下水道管網(wǎng)建設(shè),現(xiàn)在要求排水標(biāo)準(zhǔn)是“五至十年一遇”,但實際上很難在每個區(qū)域?qū)崿F(xiàn),再比如城市抗震防災(zāi)設(shè)防的新標(biāo)準(zhǔn)、城中村改造,也很難統(tǒng)一要求。
另一方面,現(xiàn)有的防災(zāi)標(biāo)準(zhǔn)不可能一味升級,當(dāng)災(zāi)害超越設(shè)防標(biāo)準(zhǔn)以后,同樣需要做好預(yù)案。“我們每個部門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都很強,但部門和部門之間的協(xié)同整合能力相對有限,在災(zāi)害到來時這種配合上的參差會帶來更多損失。”他說,同時,很多關(guān)于防災(zāi)減災(zāi)的規(guī)劃和培訓(xùn)在一線城市落實較好,但更多地方還沒意識到應(yīng)對氣候災(zāi)害的重要性。
“無論是氣候還是其他宏觀政策,往下落到具體社區(qū)以及人們的生活中時往往會變成特別紛繁復(fù)雜的家長里短,涉及到一個個具體的人的生活。”來自能源基金會的姜冰說,從規(guī)劃的角度來說,落實政策基本單位是街道,一個街道可能有幾個小區(qū),或者一個街道只有一個比較大的小區(qū),每個街道的情況都不太一樣,具體一個政策落到街道時會細碎到何種程度,甚至有沒有落到街道,都需要畫個問號。
二、缺位的氣候視角 自2007年《中國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》提出堅持減緩與適應(yīng)并重原則以來,我國在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開展了大量工作——氣候?減緩?旨在減少或限制溫室氣體排放,?適應(yīng)的目標(biāo)則是確保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能夠適應(yīng)已發(fā)生和預(yù)期的氣候變化。這兩個對策相輔相成,同時也與城市更新息息相關(guān)。
但無論是在抗災(zāi)備災(zāi)還是城市更新實踐中,相關(guān)視角仍存在缺位。
在北京房山洪災(zāi)現(xiàn)場,郝南和隊友們見證了爆發(fā)式山洪留下的痕跡——十米來寬的河谷,平時只有涓涓細流,災(zāi)后河床下切了5米多;在之前響應(yīng)過的各種山洪災(zāi)害中,也領(lǐng)教過爆發(fā)式山洪的威力:“幸存者描述,深夜里浪頭涌過來有6米多高。”他回憶,山洪一過,不管是磚瓦房還是水泥房子,三層樓就只留下地面的瓷磚。這是一種超出認知和經(jīng)驗、甚至有些“超現(xiàn)實”的場景。
然而,正是這些會帶來創(chuàng)傷的“負面”信息,往往被人們潛意識地排斥,只有一些偶爾形成熱點的災(zāi)害中的個別事件能被媒體和公眾看見,在認知和實踐層面,未有經(jīng)歷的社區(qū)和居民應(yīng)對極端氣候的經(jīng)驗都是缺失的。
在城市更新工程中,居民也常常成為消極被動的角色。
北規(guī)院弘都院中心高級工程師、城市規(guī)劃專業(yè)碩士王虹光提到,這不僅是因為國內(nèi)很多社區(qū)建筑基礎(chǔ)薄弱,也是因為目前大家對于氣候變化的認知不充分,在老舊小區(qū)改造的過程中往往照顧不到居民關(guān)心的細節(jié),比如陽臺漏雨、地下室積水等。往往只有在問題發(fā)生后,才會想辦法補救。
在國內(nèi),很多社區(qū)尤其老舊小區(qū)在建設(shè)時相關(guān)標(biāo)準(zhǔn)還未完善,樓體結(jié)構(gòu)相對脆弱,經(jīng)歷時間的打磨,墻體和管道逐漸老化,雨季可能面臨漏水等問題,等到高溫天氣用電高峰時,這類小區(qū)又面臨著電力不足的問題。
另一方面,老舊小區(qū)多無專業(yè)運營管理團隊,公共空間和運行模式不夠完善,這時如做一些結(jié)構(gòu)加固、外立面整修等更新改造工程、需要共識甚至共同出錢的,便容易陷入僵局。
“過往,可能只需要考慮城市更新,但氣候變化的影響如此巨大,城市更新不得不以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為新切入點考慮。”能源基金會策略傳播項目主管姜冰提到,因此,城市更新的內(nèi)容發(fā)生了變化并有了面向雙碳的新目標(biāo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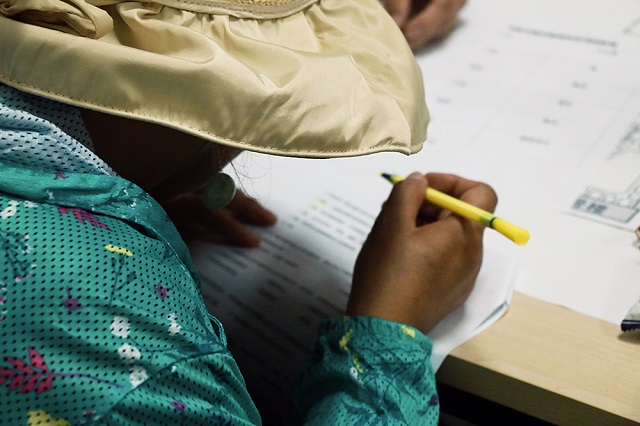
在能源基金會的支持下,北規(guī)院弘都規(guī)劃建筑設(shè)計研究院在北京三個社區(qū)開展了氣候適應(yīng)的相關(guān)試點項目。
今年,在能源基金會的支持下,北規(guī)院弘都規(guī)劃建筑設(shè)計研究院在北京三個社區(qū)開展了試點項目,分別是以老年人居多的平房為主的傳統(tǒng)街坊式社區(qū)a,包含新舊住宅和老年人年輕人的混合式社區(qū)b,基礎(chǔ)設(shè)施較完備,居住群體較年輕的現(xiàn)代商品房社區(qū)c。
“如何從‘氣候變化’的角度看待社區(qū)建設(shè),怎么將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加入到城市更新過程中,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,也是項目的初衷。”姜冰說,大家對于氣候變化的認知和接受程度不算太高,但它可能是在更高層次、能切實改變居民生活的一個理念。“我們希望將城市更新和氣候友好城市相結(jié)合,找到二者協(xié)同發(fā)展的路徑。”

在能源基金會的支持下,北規(guī)院弘都規(guī)劃建筑設(shè)計研究院在北京三個社區(qū)開展了氣候適應(yīng)的相關(guān)試點項目。

在能源基金會的支持下,北規(guī)院弘都規(guī)劃建筑設(shè)計研究院在北京三個社區(qū)開展了氣候適應(yīng)的相關(guān)試點項目。
三、找到風(fēng)險點 正因氣候視角的缺位,以提升居民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的自主性為目的的科普和啟蒙愈發(fā)重要,同時,作為減災(zāi)行動基本單元和韌性提升關(guān)鍵力量的社區(qū),自身能動性也有待激發(fā)。
“社區(qū)一定要站在居民的角度,讓他們了解到氣候和自身的相關(guān)性。”翟國方說,人對風(fēng)險的認知總有僥幸心理,這也是需要提升公眾認知的部分,這不是一個純自上而下的問題,而是上層政策和居民共同發(fā)力,需要雙方對風(fēng)險的認識達成一致。
在北京的前述三個社區(qū)試點實踐中,幫助居民“找到風(fēng)險點”也是重要一環(huán)。
清華大學(xué)建筑學(xué)院副教授劉佳燕長期從事城鄉(xiāng)規(guī)劃與社會學(xué)交叉學(xué)科研究與實踐,她帶領(lǐng)團隊參與了前述試點社區(qū)的工作。
劉佳燕說,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或風(fēng)雹,往往能放大那些日常中易被忽視的安全隱患,比如年邁而脆弱的老樹、搖搖欲墜的井蓋,或是受損、老化的室外電器設(shè)施等,將其瞬間轉(zhuǎn)化為歸家途中的致命威脅。“我們需要提醒居民尤其是脆弱群體認知到這些風(fēng)險點,同時要了解作為一個個行動主體來說,他們又是如何認知氣候問題和風(fēng)險的。”
她認為,需從社區(qū)和群體這些更精細的顆粒度出發(fā),關(guān)注不同地區(qū)、人群面對極端天氣事件的預(yù)防、應(yīng)對和恢復(fù)能力,特別要關(guān)注其中的脆弱地區(qū)和群體——他們聚集在哪些地方,在社區(qū)的居住狀況和社區(qū)的配套設(shè)施是怎樣的,可能面臨哪些風(fēng)險。“比如大量老舊小區(qū)里的老人孩子、高溫天氣下的外賣小哥,都屬于我們所說的脆弱群體,需要在城市整體環(huán)境提升和資源配置中予以重點關(guān)注,背后的理念就是‘氣候公正’。”
“我們想要根據(jù)不同社區(qū)的類型,去研究不同社區(qū)類型面對極端天氣時不同人群的韌性訴求是什么。另一方面,從社區(qū)層面考慮氣候應(yīng)對建設(shè)指引,也是對現(xiàn)有上位政策的一種回應(yīng)和補充。”北規(guī)院弘都規(guī)劃建筑設(shè)計研究院品牌策劃與社區(qū)培育中心組的趙琳介紹,2023年起,他們便開展社區(qū)氣候應(yīng)對變化能力研究,研究在北京選取了三個典型社區(qū)進行調(diào)研走訪。
趙琳所在的研究團隊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有社區(qū)氣候應(yīng)對層面,在治理機制、建筑基礎(chǔ)設(shè)施、居民自主提升應(yīng)對能力幾個方面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。
調(diào)研走訪中,社區(qū)居民的訴求更加具體。
趙琳說,在試點的三個社區(qū)中,居民普遍感受深刻的問題有“夏天熱得不能出門”“相對于前幾年更熱”,也能明確的說出“全球變暖”這樣的名詞。有居民提到,樹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車,冬天出小區(qū)門會被冰滑倒,以及墻皮脫落和小區(qū)公共空間裸露的地皮風(fēng)沙太大等問題。類似樹木倒伏這樣的現(xiàn)象,居民會直接反映給社區(qū),社區(qū)也會派專人處理。
在硬性設(shè)施上,居民們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建筑、道路等基礎(chǔ)設(shè)施上。趙琳介紹,調(diào)研社區(qū)中,存在建筑老舊、管網(wǎng)外露等情況,在極端天氣發(fā)生后,部分居民反映,會出現(xiàn)建筑滲水漏水、設(shè)施漏電等現(xiàn)象。
“我們在對應(yīng)的社區(qū)舉辦了三次工作坊活動,來的很多都是老年人。”趙琳記得,在中心城區(qū)b的活動上,他們遇到了一個八九十歲的奶奶,表述能力強、邏輯清楚,具備氣候應(yīng)對知識,也愿意向大家傳達正向的觀念,讓工作人員們印象深刻。“我們覺得這種有倡議意識的老人,可以作為很好的志愿者和活動引領(lǐng)者。”趙琳說,這類個體自身具備一定的知識體系,另一方面大家也愿意聽她的建議,她能把相似共識的人聚在一起做事,是發(fā)揮居民自主能動性的一種措施。
四、探索中的更新思路 類似的實踐也在上海展開。

上海交通大學(xué)設(shè)計學(xué)院可持續(xù)生態(tài)設(shè)計中心主任車生泉教授告訴澎湃新聞,今年他們參與上海市規(guī)劃設(shè)計研究院組織的上海城市空間藝術(shù)季聯(lián)創(chuàng)實驗室項目,在南京西路街道和江蘇路街道的兩個社區(qū)做了關(guān)于氣候適應(yīng)性的調(diào)研,內(nèi)容包括居民對高溫?zé)崂说恼J知、社區(qū)的綠化情況、環(huán)境調(diào)查和氣候風(fēng)險模擬等,試圖探討社區(qū)怎么適應(yīng)高溫?zé)崂耍屓四芨孢m的生活。

調(diào)研團隊發(fā)現(xiàn),不同社區(qū)的情況有差異,但共同的風(fēng)險是高溫?zé)崂颂鞖鈱】涤绕涫谴嗳跞巳簬淼耐{。
“有些社區(qū)比較老舊,以老年群體為主,社區(qū)在前期規(guī)劃時也未考慮納入氣候適應(yīng)性相關(guān)內(nèi)容,所以我們也在尋找解決方案,看能不能在社區(qū)做一些公共空間,類似庇護所一樣的納涼的場所等等。”車生泉說,其次老年群體更容易在夏季的高溫?zé)崂讼峦话l(fā)疾病,他們希望在氣候風(fēng)險預(yù)警這塊能做更多工作;最后,在未來城市更新中,他們也計劃對社區(qū)環(huán)境做一些適應(yīng)性技術(shù)的設(shè)計,包括提高綠化遮蔭和通風(fēng)等。
在氣候變化減緩、適應(yīng)性和城市更新的交叉領(lǐng)域,相關(guān)探索一直在進行。在我國,海綿城市早在2014年便被提出,并在國內(nèi)多個城市實施。
“雨水花園、生態(tài)植草溝、透水鋪裝和生態(tài)停車場等,都屬于海綿城市的技術(shù)模塊。”車生泉舉例,像雨水花園本身也是應(yīng)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措施。氣候變化的風(fēng)險之一便是雨洪的不確定性增加,帶來暴雨洪澇災(zāi)害風(fēng)險,雨水花園一方面可以將初期降雨收集、吸納在當(dāng)?shù)厣鷳B(tài)系統(tǒng)中,減少地表徑流,這也降低了城市開發(fā)對自然生態(tài)過程的影響,實現(xiàn)低影響開發(fā)。
此外,地表徑流中的污染物也可以通過雨水花園的吸納,降低對河流污染的機會。不過他強調(diào),大的暴雨洪澇災(zāi)害無法依賴雨水花園,還是要通過防洪排澇設(shè)施對抗災(zāi)害。
趙琳提到,目前,在北京開展的試點項目主要聚焦于社區(qū)的治理體系和應(yīng)急備案系統(tǒng)、基礎(chǔ)的建筑設(shè)施、居民的自我應(yīng)對能力等,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一個社區(qū)的韌性。未來,他們希望在傳播層面,以上三個點能形成一套可復(fù)制推廣的經(jīng)驗和模式,通過媒體傳播。在宏觀層面,能充分發(fā)揮政府部門、社區(qū)、社會組織在社區(qū)治理中的作用,達成三方協(xié)作的局面,在基層治理層面進一步暢通社區(qū)治理渠道。
下一步,他們計劃在社區(qū)展開更具體的工作,比如向社區(qū)發(fā)放簡易版本的手冊,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告訴社區(qū)每一項的不足如何解決、未來有哪些可以被提升的空間;發(fā)放社區(qū)風(fēng)險點地圖,讓居民尤其是脆弱人群知曉極端天氣來之時,他們?nèi)绾我?guī)避風(fēng)險等。
規(guī)弘都院中心高級工程師王虹光同樣設(shè)想,在當(dāng)前社區(qū)試點工作的基礎(chǔ)上,未來他們也會嘗試做一系列傳播科普工作,例如社區(qū)氣候藝術(shù)節(jié)活動等。
在對更新措施的探索中,社區(qū)中的街道責(zé)任規(guī)劃師(以下簡稱責(zé)師)、規(guī)劃師成為了專業(yè)且具備橋梁作用的角色。
“責(zé)師相當(dāng)于一個探路的角色。”王虹光說,在政策落實到基層的空白地帶,他們可以做出前瞻性的實踐,同時又可以將實踐反饋到政策。
王虹光介紹,責(zé)師需要有一定專業(yè)技能,一方面可以摸清社區(qū)的基本情況,協(xié)同居民的需求,幫助外來技術(shù)團隊共同推進實踐和試點;另一方面,責(zé)師可以將實踐獲得的經(jīng)驗反饋到上級部門、反映到政策中。“比如我們提到的老舊小區(qū)改造中缺乏氣候變化相應(yīng)的內(nèi)容,責(zé)師也可以將相關(guān)的經(jīng)驗反饋,未來或許就能完善相關(guān)領(lǐng)域的政策。”她說。
她介紹,在北京,責(zé)師基本是全覆蓋的,有些責(zé)師會負責(zé)多個區(qū)域,有些責(zé)師長期駐扎在一個地方,或是某個單位派出的一位專家,他們可以通過搭建平臺的方式,引入更多的力量。“現(xiàn)在北京還在推動‘多師協(xié)同’,未來可能會出現(xiàn)建筑師、經(jīng)濟師和景觀師等不同角色協(xié)同工作,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基層的問題,推動項目的更新落地。”
五、社區(qū)中的主動性、彈性和冗余量
“社區(qū)絕非被動接受規(guī)劃和改造的客體,而是充滿主動意識和行動能力的主體。”
清華大學(xué)建筑學(xué)院副教授劉佳燕說,研究者、規(guī)劃師應(yīng)秉持扎根社區(qū)的理念,通過深入調(diào)研、積極互動和協(xié)同行動,真誠傾聽其聲音與需求,精準(zhǔn)把握每個社區(qū)的獨特稟賦、資源底蘊和發(fā)展能力,從而量身定制出既符合地方特色又切實有效的應(yīng)對策略。
“比如我們經(jīng)常聽到氣象災(zāi)害中的紅、橙、黃、藍四色預(yù)警信號,但很少有人能清楚講出它們的具體含義和區(qū)別,以及該采取哪些對應(yīng)的個體行動。這凸顯了專業(yè)氣象預(yù)報傳遞和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過程中,亟待建構(gòu)清晰、有效的知識傳播和認知橋梁。”
劉佳燕說,這種差異性深刻揭示了專業(yè)術(shù)語和日常生活語言之間的鴻溝——如何讓民眾真正理解這些專業(yè)名詞折射到生活中,會對自己造成什么樣的影響,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下采取適宜的應(yīng)對舉措。“所以,構(gòu)建從專業(yè)知識到日常行動的高效傳導(dǎo)機制,亟需一套通俗易懂、貼近生活的科普語言體系。
車生泉同樣強調(diào)了居民參與的重要性。
“技術(shù)是理性和機械的,它為當(dāng)?shù)氐木用袼邮艿倪^程,也是一個社會化、一體化的過程。”車生泉說,在氣候適應(yīng)性方面,除了項目本身,落點還應(yīng)該在人身上。“通過提升與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和健康相關(guān)的氣候適應(yīng)性和環(huán)境舒適性,他們能直接感受的是這個社區(qū)的具體改變。”
另一方面,未來的氣候變化,不確定性增強是一個顯著特征。劉佳燕說,為應(yīng)對這種不確定性,社區(qū)規(guī)劃和更新需要融入更多彈性元素,此外,并非所有建筑和設(shè)施都要按照幾百年一遇的標(biāo)準(zhǔn)來建造,這背后是高昂成本和資源有限性的雙重挑戰(zhàn)。
劉佳燕提到,我們需要轉(zhuǎn)向更智慧和可持續(xù)的應(yīng)對策略。一方面,汲取中國傳統(tǒng)營城理念中天人合一、和諧共生的智慧,強調(diào)預(yù)防為先,增強城市與環(huán)境的適應(yīng)性;另一方面,積極推廣“平急兩用”的規(guī)劃建設(shè)理念,確保社區(qū)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在平時服務(wù)居民生活,緊急時刻能迅速轉(zhuǎn)化為有效的防災(zāi)避險資源。例如,日常供居民休閑的小綠地、小廣場,在災(zāi)害發(fā)生時可以靈活轉(zhuǎn)變?yōu)榕R時的避難空間,這需要跨部門、多專業(yè)力量從規(guī)劃、建設(shè)到后期運維管理的緊密協(xié)作和統(tǒng)籌考量。
除了“主動”和“彈性”,城市的“冗余量”也是時常被提起的概念。
王虹光解釋,“冗余量”概念可以被應(yīng)用在韌性城市中,比如防災(zāi)標(biāo)準(zhǔn)以下,我們的城市建筑足夠牢固可以防得住災(zāi)害,但如果災(zāi)害超出了這個標(biāo)準(zhǔn),城市也不會崩塌。它仍然能留出一定的彈性和余量,在災(zāi)害稍微超過一點的時候,城市仍然能夠正常運轉(zhuǎn),提供一些基本功能。
更大的城市尺度上,社區(qū)同樣可以多做一點,比如打造降溫遮陰和急救設(shè)施,布置臨近的水源,為社區(qū)內(nèi)的老人兒童玩耍時中暑時提供簡易的應(yīng)急救助,而對于戶外工作者比如保安、保潔、快遞、外賣員以及農(nóng)民等脆弱人群,也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喝水庇蔭的地方,降低他們應(yīng)對極端天氣的風(fēng)險。
“城市面臨高溫時,有些人群會選擇去商場、地鐵站乘涼,本來這些場所的功能可能不是這樣的。但它具備這個功能之后,市民也能真正享受到好處。”王虹光說,如果城市的公共空間能形成有機網(wǎng)絡(luò),尤其是一些社區(qū)的冗余空間被利用起來,整個氣候應(yīng)對能力也會相應(yīng)提升。
當(dāng)然,除了一時的創(chuàng)意,社區(qū)乃至整個社會需要有一個動力能讓這些機制持續(xù)發(fā)揮作用,當(dāng)共識漸漸形成,很多互助可以自然而然、不在機制催促的情況下發(fā)生。“如果社會形成了這種共識,人和人之間的鏈接可以互為安全保障,平常可能用不上,但突發(fā)情況來臨時,這種社區(qū)韌性治理會發(fā)揮極大作用。”她說。
來源:澎湃新聞



